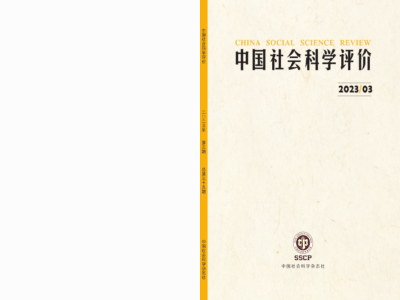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欧博官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出版《第二自我》(The Second Self),推动学界关注技术与自我的关系。特克尔将计算机称为人类的“第二自我”,认为每个人都将有机会以某种方式与计算机交互,而计算机可以映射自我,充当心灵的一面镜子。此后,随着计算机虚拟社区、聊天室等应用的开发与推广,特克尔又率先关注用户的在线角色扮演与自我的关系。她发现人们的自我认同不再是单一的,匿名的虚拟环境使得用户可以选择自己想扮演的角色。他们不再局限于现实的身体与自我约束,而可以打造多个身份模式。随后,人们开发了各种数字技术将自我数字化,数字自我的表征形式也随之复杂。 如今,数字技术已经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对自我构建产生重要影响。个体自我不仅有意识地活跃于虚拟世界中的角色扮演及其互动,还在无意识中被数字技术建构并开展对应行动。从现实角度而言,网民与非网民都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在互联网环境中,分别主动、被动地构建着数字自我。自我变化所引发的自我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变迁以及如何应对,是本文的现实关切。从学理角度而言,学界关于数字自我的研究要么停留在单一的理论阐释,要么局限于现象描述,单一化和经验化明显,整体性理论研究不足。在被技术包裹的环境中,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全面认知数字自我,如何回应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自我特征,为什么数字自我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中产生相较于传统自我而言更强的行动驱使能力,学界应当如何面对数字自我的发展趋势,这是本文的学术关切。接下来,本文将分析数字自我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内涵、形象特征以及产生行动驱使能力的原因,提供研究数字自我的社会学方案。 一、数字自我的背景与内涵 当前,以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人类逐渐迈入人工智能时代。从语音助手到生成式人工智能、从扫地机器人到智慧家居、无人工厂和自动驾驶等都说明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创新的产物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此同时,中国网民数量飞速增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已经进入数字生活,并在网络上具有某种自我身份。 数字技术是当今社会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趋势的技术基础,对数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相较于工业时代的自我构建,如今人们获取信息和制造数据的能力前所未有。数字技术不仅制造生活意义,同时又抽离生活意义。因此,若要了解数字化转型的过程,需要将研究视野拉回至微观的主体性研究,理解数字社会运行的微观机制。 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数字自我的两个方向开展。第一个方向关注数字自我与内在自我(即非数字自我)的关系,分析数字自我是内在自我的拓展还是与内在自我的融合。第二个方向关注数字自我的延伸范围,欧博聚焦数字自我是单一的表现形式还是多元的实践形式。 在数字自我与内在自我的关系层面,有学者认为,数字自我是个人内在自我的扩展或向外延伸。内在自我更加聚焦来自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关系,数字自我更加强调虚拟世界中的体验。即用户在虚拟世界时,此时的数字自我可以经由虚拟形象从物理世界穿越至与此相分离的虚拟世界,并与在虚拟世界中的其他用户开展实时的交流。此类说法下的数字自我与内在自我是相互割裂的,两者分离在两个世界。另有学者认为,如今已经无法将数字自我与内在自我储存库的其他方面区别开来,“数字自我”并不是说一个人的自我可以被分为物理世界的内在自我和虚拟世界的数字自我,而是要承认互联网对内在自我的影响是突出的。此类说法下的数字自我与内在自我是相互融合的,数字自我能够影响内在自我的存在与感知。 在数字自我的延伸范围层面,一类研究关注数字自我的单一构建形式,认为数字自我是在虚拟世界的角色或形象构建,个体基于对身体和自我的想象而在网络游戏等虚拟世界中塑造数字替身。另一类研究认为数字自我的内涵不断丰富,不仅涉及个体在虚拟世界中的自我投射,还涉及多种实践形式。比如,有学者不仅认为个体创建虚拟形象以及在数字空间中的互动是个体探索自我和解放自我的形式,还认为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自拍而被他人凝视时是一种将自我客观化的形式,等等。总的来说,无论是单一的数字自我表现形式还是多元的数字自我实践形式,学界已经共同认识到数字技术对个体自我构建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延续学界关于数字自我概念的现有探讨。关于第一个方向,本文倾向于将数字自我视为与内在自我的融合,认为数字自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或呈现内在自我。数字自我是用户在人工智能时代与技术互动时产生的自我,它不再孤立于虚拟世界或现实世界,而是与虚拟世界及其现实世界网络紧密相连,与内在自我一同构成自我概念。关于第二个方向,本文倾向于将数字自我视为多元的实践形式,具有一定的行动驱使能力。为聚焦数字自我的社会学理论探讨,本文不涉及对非网民被动构建数字自我的内容。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数字自我”的内涵界定为个体受数字技术应用及其互动的影响而构建与呈现的自我形象,具有一定的行动驱使能力。 二、数字自我的形象特征与理论传统 社会学家始终关注个体互动中的“自我”研究,涉及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人际互动的交往模式,调整人类自我的构建方式。因此,“自我”的经典理论为数字自我的研究提供理论根基,数字自我为经典理论注入时代活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自我在社会性的基础上发展出虚实融合的自我,在规训性的基础上发展出量化的自我,在自反性的基础上发展出极化的自我。 (一)虚实融合的自我:社会性 数字自我的第一个理论传统是社会性自我,即探讨自我的社会属性。库利认为社会性自我是心灵对自身产生于交际生活的某种思想或者思想体系。它取决于个人对所想象的他人的意识的态度,这可以视为一种“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彼此映照着对方。”我们在镜子中看到并乐于看到我们的面容、身材和着装,欧博娱乐是因为这些形象是我们的,同时,我们会根据这些形象是否满足了我们所期待它们的那样而产生满意感或不满意感。米德认为当人们接触到一个人的自我时,就是接触到了某类行动、某种社会过程。人们会将他人对自我的期望内在化,呈现出被动的社会建构过程。戈夫曼也强调自我结构(“我们向他人呈现我们自己”)需要在日常生活的“表演”中探索。在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技术催动社会场景空间不断变化,人类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如何呈现自我形象,又会如何将他人的期望内在化? 数字自我可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拓展与探索自我。数字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打造了进入虚拟世界的可能,它会影响人们的自我感知和自我构建。虚拟世界犹如一张银幕,人们可以在这个银幕上投射不同版本的自我和自我的各种想象,但这种投射可能具有反作用,并对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认知产生影响。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进步,用户探索数字自我的体验将更加真实,这种虚拟体验不仅来源于虚拟世界,还来自物理身体且深刻地影响着身体的感觉。 数字自我能够在视觉上实现在线自我呈现。用户在社交媒体上传的自我图像(或者是“自拍”),被视为自我呈现的一种形式:向他人展示他们是谁的一种方式。同时,人们也从线上互动中的外部环境来打量自己。用户在社交媒体上以取悦目的来展示身体,是一种自我呈现客观化的形式。如果用户因在社交媒体上呈现客观化的自我形象而获得更多的“点赞数”,那么这种积极反馈会激励用户取悦观众。用户会像经营品牌一样打造和维持自己在网络上的身份和形象,在符合观众期望的背景下实现“自我商品化”。 数字自我帮助人们重新感知死亡的概念。在人类生命历程的终点,逝者也正在实现一种“在线永生”。一个人的死亡可以通过大量在线媒体进行宣布和纪念,例如Facebook主页经常被用于纪念逝者。但“在线永生”并非意味着用户就能长存于世界,而是可以用来思考数字自我与数字基础设施的关系。作为物理的自我已经与数字基础设施无法完全二元分割,不同生命形式的感知已经紧密交织在一起。由于“数字”最终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目前人们从视觉上见到的数字客体存在是极其脆弱的。进一步而言,当数字基础设施消失,意味着数字自我在数字技术的承载平台也便消失,那么用户搭建的角色形象或他者在此空间的情感寄托将无处安放,用户的数字自我也伴随对应数字基础设施的消失而部分“死亡”。 由上可知,数字自我沿袭传统理论中的社会性,在自我构建上更加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自我在特定场景中所拥有的某种形象与传统自我理论相同。这种形象构建来源于日常生活、他人期待或者自身基于社会环境的想象。但是,数字自我更加强调对数字基础设施的依赖。数字自我拓展了自我形象构建的可能性,人们可以借助于数字技术的多元场景或应用产品而形成不同的角色和自我定位。数字自我扩大了将他人期望内在化的程度。传统自我在人际互动中面对的期望是有限的,数字自我面对的期待是无限的、未知的。人们的形象不仅要在真实的个体观察下被凝视,还在机器审查中被观望。 (二)量化的自我:规训性 数字自我的第二个理论传统是规训性自我,即在身体规训下的自我。福柯提出自我规训技术,包括一种控制模式。这种控制模式意味着一种不间断的、持续的强制,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驯顺关系。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或者在他人的帮助下,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思想、行为和存在方式进行一定数量的改变操作,欧博allbet从而达到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发展出一种关于“自我的技术”,尽可能地反观自己与监视自身所经历的一切。在人工智能时代,普通个人是否在众多观看中规训着自己的身体?又借助何种手段来控制自己的身体、灵魂与自我? 数字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自我塑造以及体验具身化自我的方式。当人们的自我逐渐数字化,更加微粒的监视就变得不足为奇。正如鲍曼与里昂所传达的:社会中的监视不再是单向的权力行使过程,它无处不在,渗透到许多原本难以企及的生活领域。勒普顿以社交媒体上的自愿观看实践为例,认为这种自我塑造实践是在运用数字设备的社交媒体参与和自我跟踪策略中进行的。许多用户自愿加入相互观看或自我监视。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跟进他人的信息和状态,同时也接受着他人的关注和审视,希望别人关注并评论自己的内容。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塑造的意义,就是让观众来审视所发布的内容并给予回应。 数字自我正在日益互联的身体中构建。当我们谈到自我时,很难逃脱自我的物理栖息地——身体来谈论。因为自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本体肉身的感知、认知、认同。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身体逐渐脱离于过去单独存在的肉身概念,而形成一种身体互联的趋势,这在当下被称为“身体互联网”。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熟知的身体互联网的例子是用于身体外部的设备,如智能手表、健身跟踪设备等。移动互联的技术使人们的外在规训策略发生转变。比如,健身跟踪设备一方面把健身者从健身房中解放出来,将自我规训的空间延展至生活领域,另一方面借助软件的去人格化达到近似标准的完美。越来越多的个人借助数字设备对身体数据进行收集和追踪,如体能活动、心率、睡眠模式等,这种通过数字技术对自我进行测量和记录的实践被称为“量化自我”。 数字自我正在成为一种以数据为导向的自我,人类的自主性受到技术与社会的双重规制。从技术视角来看,数字自我深受数字技术的影响。在技术强有力的渗透下,自我与他者、人类与机器、身体与技术的边界已日益模糊。谁才是最了解你的人,是作为人类的主体还是作为机器的客体?当一个人的自我需要时刻依赖数字技术及其应用来感知自我存在、认知自我状态,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算法数据调节着自我行为时,人类是否在向技术让渡自我的隐私与自由?从社会视角来看,数字自我强调通过数字技术加强对自我的监测和规训,这是自我提升的良好方式,但是数字自我更加信赖的是主观体验还是科学指标数据?后者似乎更胜一筹。正如贝里所强调的,人们通过持续的自我规训,不断再生产着社会文化认可的自我形象。 由上可知,数字自我沿袭传统理论中的规训性,在自我管理上更加强调量化与数据。数字自我在被“自我的技术”管理时与传统自我理论相同。人们在看不见的、无形的“瞭望塔”中被监视。拥有数字自我的个体也在众多凝视下找寻、调整自我并规范自身行为。相较于传统自我,数字自我更加强调自我管理的持续性,对身体的量化程度前所未有。传统自我管理借助的技术工具仅是外在的,不论是全景敞视监狱还是指标计量工具,它们都抽离于个体肉身来管理自我。数字自我借助的数字技术工具既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嵌入的。这不仅扩大了自我对身体和行动过程的跟踪范围,还能够呈现出比自身描绘更加全面且准确的可视化数据。这种身体数据化的过程使原本模糊的行动变得清晰可见,有助于用户实现自我赋权。 (三)极化的自我:自反性 数字自我的第三个理论传统是自反性自我,即在自反性现代化中探讨的自我认同。在贝克看来,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种个体化时代,既有的社会形式逐渐解体,比如阶级、社会地位、性别角色、家庭、邻里等范畴日趋弱化。然而,这种看似个体化的特征,仍然需要与社会背景相结合而表现出来。尽管每个人都在进一步个性化、零散化,但是人们也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我们”出现。这种新式的“我们”建立在信息和交流结构上,是一种基于社群基础、具有共享意义的自反性理解,它关系到一种阐释性的自反性,是增强的文化结构对自我的影响。人们或者在集体中观照自己的独特特征或者在公共事件中定位自我。在人工智能时代,个体所处的社群集体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人们如何在社会背景中展示自反性? 数字自我正在新型社群与集体身份中扎根。一方面,数字自我在新型社群中相互依赖。互联网用户可以根据兴趣爱好、专业特长等打造新型社会互动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用户可以依据群体确立的规范与价值观来确认自我身份与认同。另一方面,数字自我基于原有的集体身份寻求精神共鸣。比如,海外侨民可以通过数字技术的连通性改变用户的空间感、归属感与自我认同感,实现在故乡空间范围之外人们的情感联结和集体身份的维系。那些具有同样身份认同或情感支撑的用户在数字空间中表达着自我的诉求,人们的行为会基于集体记忆来汇集成集体符号而不是个人的单独行动。 数字自我在群体极化中迸发情绪化表达。社交媒体中的在线互动为形成极端主义小团体提供土壤。人们在同质化的信息中强化自己的观点,追寻与自我相契合的观点或行为。这种类似于灵魂共振的自我体验在数字空间中愈演愈烈。比如,极端主义小团体通过互相联络、互相声援、共同向反对者发起攻击而形成归属感,并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加偏激。如此一来,互联网环境看似是开放的,实际上是有利于保存一个相对闭合的社会网络。日常生活需要构建真实的异质而开放的虚拟社会网络。 数字自我具有行动驱使能力,而且具有快速传播、聚集的特性。用户的点击行为(点赞、评论、转发等)是一种对事件的态度或情绪化表达形式,这其中夹杂着用户复杂的情感,它具有从点击行为转向集会行动的弹性。因为数字空间的信息传播和物理空间的行动实践为集会行动赋予强大力量,它能够迅速将行动者从数字空间集结到物理空间,这提升了行动者的参与性和持续性。社交媒体有助于充满个体化、在地化和特定共同体分歧的社会运动转向一个具有集体意识的结构化运动,即拥有共同的不满和行动机会。 由上可知,数字自我沿袭传统理论中的自反性,在行动驱使能力上更加极化并具集聚性。数字自我虽然看似一个微观的个体化概念,但它同自反性中所表达的“我们”相同,离不开整合的社会环境。拥有自反性的个体会因为兴趣、观点等区别于传统的社会形式而聚集在一起,从而找寻自身的价值。人们在这个找寻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审视自己的特征与行为,塑造自身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如此一来,出现立场相同的极端主义团体便不足为奇。相较于传统自我形成的社会环境,数字自我的土壤更加多元。人们既生存在一个共有的数字空间中,又割裂在不同的观念群体中。数字技术扩大了数字自我产生行动驱使能力的可能性。相近的个体会通过自反性在大量的公共事件或信息中观照自我,并在一定情绪引导下形成集体行动,出现线上声援、线下聚集的情况。 三、数字自我的行动驱使能力与研究方案 数字化转型进程离不开数字应用的微观个体。数字化转型之所以能够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是因为有无数个体的加入,铸造着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因此,若要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特征,就要关注到个体数字自我的复杂面向,关注数字自我对现实的影响力。 (一)数字自我具有行动驱使能力的社会基础 正如贝克等在《自反性现代化》中所强调的,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能动者所获得的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便越大,改变社会状况的能力也越大。相较于传统自我概念,数字自我能够在现实中产生强大行动驱使能力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总结而言可以归类为三点,分别是:时空重组、阶层重置、情绪共鸣。 首先,时空重组为数字自我提供空间可能性。在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人们的社会互动与身份认同构建主要是基于在地空间的血缘、地缘和业缘,可以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预判到行动者的形象与行为结果。但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一种新型的交往关系——“信缘”逐渐出现。个体能够经由互联网或者其他信息互联通道而结成新的群体类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个体成为数字网络的基本节点,推动形成以个体为独立单位的新的社会形态。人们的社会互动环境变得复杂。数字技术为个体交往同时提供了“时空拓展”与“时空压缩”的空间体验。一方面,数字技术搭建了自我认同的共时性平台。人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发展和维系与他人的关系,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自我认同感能够打破“在场”与“缺场”的边界,建立长久的连接关系。个体虽然身处不同的时间区域、接收着不同的地方性信息,但是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聚集于同一个时空互动场域,共用数字空间中的时间和信息表达。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模糊了影响自我构建的空间边界。我们正处于“在线生活”(onlife),线上线下的界线将越来越模糊,最终消失。这种持续在线的生活让个体在同一场合下可能要转换多重自我形象。比如,数字技术模糊个体在工作与生活中的边界。这种工作入侵生活空间、私人交流进入工作场域的情况,使得人们在多种角色转换时可能承受额外的压力。 其次,阶层重置为数字自我提供组织可能性。在传统自我的行动图景中,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影响着自我认知和对应的行动权限,较难突破年龄、职业、宗族等社会结构的限制。然而,在数字自我的行动图景中,传统的结构限制被部分消解,现实世界的社会地位并非直接复制在数字空间中。也就是说,数字自我中的社会流动属性打破结构限制,实现阶层重组。因此,数字自我的行动驱使能力可能受到新型阶层的权力影响。一方面,那些掌握数字技术的编程精英可能成为主导数字世界的力量之一。他们的设计思想以及形成的产品,影响着个体在使用产品以及之后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不懂数字技术或较晚进入数字世界的人群,可能会成为数字世界的弱势群体。这意味着接入互联网的个体具有了表达诉求与开展行动的新渠道,但也在形成新的不平等形式。 最后,情绪共鸣为数字自我提供联结可能性。有研究指出,人们能够在数字空间中产生持久性行动的本质原因在于行动者本身的共同信念和理想等非数字化因素。在传统集体行动中,内部成员之间具有明确的界限和分工,有内圈和外圈之分,参与人数和能量有限;社交媒体则模糊了集体行动的内外边界,大多数想参与的行动者都拥有对事件的发声渠道,这扩大了集体行动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在公共事件通过数字应用进入个体视野之后,个体会自动在事件中观照自我,并生成对应的认同感和情感反应。当充满情绪的数字自我达到一定程度时,会推动具有代表性情绪的个体行为迅速集结为集体行动。因此,数字自我在集体行动领域发挥着内在情感联结的作用,其影响力不可忽视。 数字自我并非总是积极向上的,也会在现实中产生消极行为。首先,人们可能会在繁杂的数字世界和信息海洋中迷失自我,缺少现实交往的动力。个体长期生存在数字世界中,部分情感需求在虚拟的数字世界中消解,而忽略现实物理空间的社会关系,缺少相应的交往与互动能力。由于数字世界的虚拟性程度更高,个体自我的虚无感表现强烈。比如,家庭成员沉迷于手机,成员间的互动和对彼此的了解减少,在亲密感支撑上稍显不足;又如社交恐惧症、社会性死亡等体验增多。其次,人工智能技术增加数字自我的复杂性,易使个体失去明辨是非的能力。网络谣言和信息诈骗等现象是数字世界的毒瘤之一,引导人们走入“后真相”时代。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和人脸识别等多重技术路径,能够实现对个体的声音、容貌和肢体行为的复刻。这意味着个体和交往对象的“数字自我”的唯一性和真实性难以保障。最后,数字世界中的注意力经济正在极度攫取个体的情绪价值。比如,信息平台的内容制造者为提升点击量和流量,在内容呈现上不择手段。明面上虚实融合的世界已然对数字自我产生消极影响,而暗网对数字自我的危害性更加值得关注,血腥与暴力乃至引导自杀行为的风险需要被干预。因此,人们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加强对数字自我的研究。 (二)面向数字自我的社会学方案 社会学研究者可以从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个层面入手,为发展健康的数字自我提供学理支撑。 首先,重视数字自我的学术研究,细化认知数字化转型的颗粒度。目前学界对数字自我的微观研究重视不足,而在已有的数字自我研究中又出现明显的断裂现象,研究触角较少涉及真实的个体。有研究采用大数据方法观测到社会心态的类型,也有研究使用数字民族志的方法观察饭圈的组织行为和极化现象,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数字自我的特征开辟了道路。然而,两种研究类型存在的共性问题是:(1)研究场域局限于数字世界,呈现出的研究结果基本为描述性内容,缺少与现实世界的因果性研究;(2)研究方法单一,尚未打破传统研究工具与新型研究方法割裂的现状。社会科学研究不缺乏数据量抑或数字空间的交往互动场景,而缺少追寻到肉身个体的结构化数据或真实的社会情境。这就意味着仅宏观地了解网络中的社会心态、价值观特征或组织行为是不够的,学者要挖掘个体背后的行为逻辑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同时,在面向微观个体的生活情境之时,仅观察到个体的物理空间行为不足以全面了解个体生活状态,需要跟踪到个体所在的数字世界以及与数字产品互动的场域中。因此,社会学者应当在宏大叙事中关注以数字自我为代表的微观旨趣研究,打破方法论壁垒,探索将传统结构化数据与大数据、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新型数据研究工具相结合的路径,开辟将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场域合二为一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数字自我的结构化影响因素,分析不同群体数字自我构建与呈现的方式与类型,为数字社会建设奠定健康坚实的底层根基。 其次,重视数字自我的政策研究,帮助提升风险治理水平。第一,推动数字社会建设。社会学者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帮助打造真正提升数字生活质量的虚实融合评估体系,设计构建有温度的“附近小世界”,提升人们在物理空间的感知度。第二,发挥数字社会学的公共功能,积极引导个体形成正确的数字自我。第三,社会学者对社会结构的敏锐度有助于把握数字自我的发展方向,预判数字自我的性质走向,帮助建立可预判、可防范、可调适的数字自我风险响应机制。 结语 社会学要回答“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就需要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行研究。数字自我是个体受数字技术应用以及与其互动的影响而构建与呈现的自我形象,具有一定的行动驱使能力。数字自我的研究为人们理解数字生活中彼此交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提供了底层逻辑思路。数字自我意味着人们增加了一片想象力空间和自我表达的社会空间,赋予生活更加多元的意义感;但也面临着网络暴力、私刑行动、回音室效应、思维趋同与两极分化等问题。未来数字自我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比如,青少年群体的数字自我构建不容忽视,他们不仅通过移动互联网塑造、表演着自我形象,还将社会结构渗透至手机世界的信息内化于自己的生活。本文仅对数字自我的内涵展开理论探讨,内容有限。未来研究应当关注数字自我在社会关系与互动中的深层影响因素,关注在人机互动中数字自我的新可能,关注自我如何受到数字技术的规训和限制,关注情绪共鸣如何在行动驱使能力中发挥作用。这些将为回答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证基础。 (责任编辑:) |